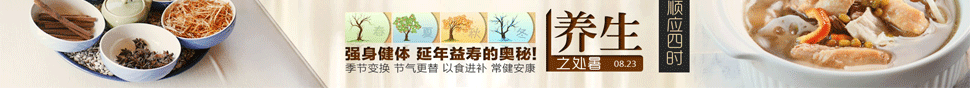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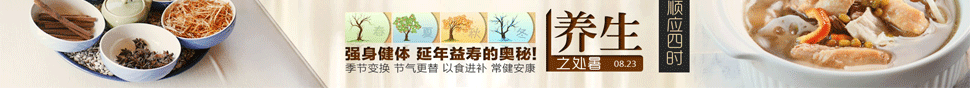
恩施城,五峰山上。
天边最后一抹彩霞散去,整个恩施城内华灯流彩,点亮每个角落。
这是八点十分的恩施,这是恩施城最惬意的时间,夜生活正式开始。
和几位朋友坐在五峰山的一家农家乐聚餐,酒已干,饭已饱。这是一个炎热的夏季,恩施城内挥汗如雨,但五峰山上晚风徐徐,清凉无比,我们凭栏看着山下的恩施城,清爽、悠闲,似乎我们并不是在一座城市的旁边。
现在的电视工作者喜欢采用的一个特技是,从早上开始把摄像机打开,录到晚上,然后把十多个小时的素材压缩,观看者会惊奇地看到:日升日落,云霞滚动……数秒钟把一天的变化尽情演绎。
电视特技很炫目,但它无论如何也比不上人的思想。坐在五峰山上,我们脑海中在闪现的不仅是一天的变化,而是恩施城几千年的变迁。
(一)
恩施城是一个狭长的冲积平坝,形如纺锤。清江自大龙潭而来,由北至南,贯穿恩施城区。
远眺清江,浩浩荡荡,宛如一条巨龙。它碧波荡漾,潮涨潮落,滋润两岸肥沃的土地,在城区形成簸箕、木鱼、擂鼓等滩。过去,夏天在清江河中游泳的人,如过江之鲫。前些年,清江闯滩又成热潮,从恩施中心出发,乘橡皮舟飘然而下,越过五段峡谷,过48道险滩,至浑水河止。一路出入激流之中,惊险刺激。十年前,我曾躬逢其盛。初上船,不免战战兢兢。要知道,在岸上远观清江,只觉其波澜不惊。到了江面,顿觉江水滔滔,船只随波浪不停摇晃。当橡皮艇冲上第一个滩头的急浪时,仿佛飞上云端,只能闭上眼睛,死死地抓住船上的绳索。
当船行数里之后,我才习惯下来,这时已经耐不住在静水中慢慢晃悠的寂寞。我们用各种方式鼓动架船的工作人员,冲向最大的险滩。结果,在某种并不太起眼的滩头,我们的橡皮艇刚刚冲上浪头,船身一侧,我从对面朋友的身上飞出船外,沉入深深的江中。幸好,我会一点水性,而清江的水又是那样清,当我浮上水面时,发现橡皮艇已经翻了一个身,工作人员正急着搜救落水的游客。
不闯滩,无法认识清江狂野的一面。也只有经过了清江闯滩,才能明白古代巴人荜路蓝缕、开拓之艰。
下午和我们一起坐起饮酒的一位朋友,多年前曾在利川发展,希望寻找到传说中的巴国古都。今年,他来到恩施,又倡言恩施城区正是古代巴国古都所在地。变化之快,胜过翻书,自然引得我们的一致鄙视。
不过,恩施城一带还真有可能是传说中的夷城。在古代文献,“施”字通“夷”。施水当为夷水,施城就是夷城。起源于清江赤穴的廪君,曾率巴人部落攻占整个清江,并创设夷城。《北堂书钞》载:“廪君乘土船下至夷城,石岸曲,水亦曲,廪君望之如穴状,曰:我既道穴中,又入此,奈何?石岸为崩,广三丈余,升级之。廪君行至上岸,岸有平石,广长五丈,休其上,投策计算处皆有石,因立城其傍。”
镦于锵锵,虎啸清江。夷城,是巴人传说中的第一个古都。夷城之设,从部落联盟走上建国之路。勇猛的巴人,自夷城出发,用一场场战争开疆拓土,书写历史。我们无法将巴国古都定在某个具体的地方,但清江中上游的恩施,必然是巴人生息繁衍之地。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自五峰上俯瞰恩施城区,仍觉得巴人不屈的战意冲天而起,高大的巴人勇士身影晃动,弓弦声、呐喊声在耳边回响。它提醒着我们,那是英雄辈出的时代。而清江河边厚厚的积沙中,或许可以找到当年战争的遗迹。
清江不仅哺育了土家族,更赋与了清江两岸儿女独特的气质。他们既有清江秀丽灵动的心灵,又有狂澜独往的勇猛。静若处子,动如脱兔。难怪道光《施南府志》说:“水惟清江为大,虽源于蜀,然蜀水多浊,而此独清,以掩映于碧波翠涛。夫山嵯峨而水清驶,其人亦宜垒砢而英多。”
不独有清江,恩施城内外溪河纵横,可以说是一个水乡。以清江为中心,山间河流如蛛丝网一样,汇聚在恩施城。宋代地理著作《方舆胜览》中除了有清江的记载处,还有关于麒麟溪、盘龙溪、铁沟等河流介绍,可见其古。
盐水溪,发源恩施城东北小渡船办事处何功伟村,长约3公里,宽约2米,自西北向东南,蜿蜒流淌,在城北一碗水处汇入清江。源头有古盐井,相传旧时有个被称作“马胡子”的人,在此熬过盐,又称马胡盐。现代研究者认为:巴人是中国历史上古老的“行盐民族”,很早就开始炼制食盐,并行销四方。而廪君在清江征战中,战胜过拥有“鱼盐之地”的盐水女神,这更给盐水溪蒙上一层神秘的光环。
它是否就是《后汉书》中记载的盐水?我们无法回答,想像当年那段缠绵的历史。
铁钩水位于城东,河流清浅,由北至南蜿蜒流淌,至南门峡口外大沙坝,汇入清江。很久以来,这条溪流被叫成喜鹊溪或洗脚溪。清嘉庆版《恩施县志》载:“铁沟水在县东三里,上有接官亭,昔为洗爵奠斝处,故又名洗爵溪。”古时,恩施出山的官道主要靠东大路,铁沟水是必经之处。北宋,乔太傅任施州知州,好友苏轼写下《铁沟行》一诗送乔太傅:“城东坡陇何所似,风吹海涛低复起。城中病守无所为,走马来寻铁沟水。铁沟水浅不容舟,恰似当年韩与侯。有鱼无鱼何足道,驾言聊复写我忧。孤村野店亦何有?欲发狂言须斗酒……”苏轼有多首诗道及恩施,生动形象,他或许到过受乔太傅之邀,到过恩施,零距离感受到恩施美丽的山水。
龙洞河源头在恩施城东郊7.5里处的龙洞。龙洞高悬在半山上,洞内渊深莫测,伏流至洞口涌出,形成数十米的瀑布,飞泻而下,跌入深潭,水雾弥漫,声势震天。过去龙洞晚上子时与白天午时洞水增涨,涨水时,声大如雷,水流喷激上射,高可数尺,随后迅折而下,势若倒海。这就是龙洞洞“子午来潮”奇观,民间传说为龙洗澡而成,故名龙洞。
自龙洞而下,龙洞河蜿蜒南流,一路青山绿水,石桥横卧,风光美不胜收。抗日战争时期,湖北省政府迁驻恩施,恩施成为战时临时省会,国民党抗战第六战区长官司令部亦设恩施。时任省主席、国民党第六战区司令的陈诚,在这里指挥第六战区军队与敌抗争,先后打响了“宜昌会战”、“鄂西会战”、“常德会战”等大小战役,重创侵略者。“鄂西大捷”后,他邀蒋介石来恩施视察战果,于半山腰修一别墅,蒋介石来恩施即居住在此,此别墅后称“陈诚公馆”。
(二)
从五峰上望去,恩施城处处皆山,高山在城外形成屏障,宛如长城环绕;中小山耸立,如盆景妆点。城中名山有回龙山、象耳山、鳌脊山、中印山之属,城西有石板岭、望城坡、客星山,城南有活龙山、天成山,城北有都亭山,城东则是著名五峰山。明代诗人黄溥记载恩施城区山水诗云:
城南山水更奇绝,客星翠若终南结。
文峰两点青插云,西岭千寻寒积雪。
翠涛丹嶂遥相连,天边隐隐开金莲。
大河一线抱城下,流觞胜迹今犹传。
良畴几处带山郭,茅屋人家尤寂寞。
麒麟溪合梅溪水,龙首五峰珠错落。
恩施城的山,多呈红色,石质较软。小时到恩施城,常惊讶地发现,山脚多开挖成整齐的洞穴,大者可圈牛马。近些年,谭庆虎老师才告诉我,这是丹霞地貌,发育于侏罗纪至第三纪的水平或缓倾的红色地层中,经长期风化剥离和流水侵蚀,形成孤立的山峰和陡峭的奇岩怪石。而最显著莫过于挂榜岩,红岩壁立,宛如张榜。相传曾有范姓书生在京考取功名,送榜公文还未到施南府,北门外悬岩上现出六个大字:“今科范生高中”,金光闪闪数日不散,前来看榜的人川流不息,锣鼓喧天,鞭炮连天,挂榜岩因此得名,而此后施南学子无论是赴省赶考还是进京会试,先要来挂榜岩看看有没有自己的名字,这岩下头从此也香火不断。
五峰山,绝对是恩施最著名的地名建筑。每次从利川至恩施,刚出马尾井隧道,远眺恩施,即可以看到群山之中,一抹翠色横于天际,比其他山峰更高。其山形,相连如贯珠,故名五峰山,又称连珠山。
入城,如果没有现代高大建筑遮挡,在恩施城区的大部分地方都可以看到它。明代施州卫世袭指挥佥事童昶《连珠山》诗:
名山连络面东开,如贯匀圆江上隈。
疑是两仪分藏宝,始知五岭露珠胎。
风来水面骊龙戏,月到天心老蚌猜。
剖腹自知非我愿,献图作赋愧无才。
五峰山控清之口,扼守要冲,自古就受到重视。宋政和年间,朝廷封五峰山神,为嘉惠侯。清清乾隆辛卯年(公元年),由太守张应桃主持在五峰上建造七级浮塔,未能成功。60年余年后,恩施知县陈肖仪等续修,才致连珠塔竣工。
连珠塔为八边砖石塔,占地面积平方米,共分7层,通高34.8米,内有螺旋石梯级,由第一层可至第七层。整个塔唯第一层最为高大,其下半部及基脚全部为巨大条块青石砌成,拱形大门高4.5米、宽2米,镌刻施南府知事吴式敏撰写的楹联:“七级庄严人际风云瞻气象,五峰卓秀天开图画助文明。”除第五层只有3个门外,其它各层均有4个高l.8米、宽0.6米的拱形门,供游客登高远望。8个塔角上各雕刻天王大力士一尊,面目狰狞,敞胸露腹,或蹲或站,双手上托,造型各具特点,无一雷同。
有了连珠塔,五峰山更加醒目。说实话,像我这样的“路痴”,如果没有连珠塔的指引,是绝对不可能在远处就认出五峰上的。而有连珠塔之助,五峰上成为踏青赏景、登高眺远的绝佳之地。昔人评恩施十景,连珠塔名列其中。民国年间《新湖北日报》刊载《记恩施五峰山十景》一文记叙说:“客有至施州者,语及五峰山之形胜,则推连珠塔焉,塔峙龙首山顶,绕以庙宇,以为守卫,下临清江,水光塔影,涟漪一片。春秋佳日,游人辄络绎于途。塔高七层,可环绕上,雾合云连,峻伟不凡。”
与五峰山对峙的是碧波峰。它矗立于江边,曲折逶迤,苍翠层涌,望之如波涛。过去山上有问月亭,相传诗仙李太白谪夜郎时,于此把酒问月,留下“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的著名诗句。为纪念这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明代施州卫抚夷同知宋洪泰在碧波峰上建问月亭以供人凭吊。清代知府王庭桢曾修,并将无敌堂改名为景李堂,于亭左增屋一椽。亭后辟一径,建亭,曰翼然亭。
李太白是否到过恩施,历来聚讼纷纭。从明代直到现在,大伙儿还在打笔墨官司,留下大量的纪录。我曾下决心把光绪版《续修施南府志》校注出来,但仅仅是“问月亭”的诗文,就把我弄得头昏脑涨,最终只能搁笔。在我看来,李太白是否到过碧波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纪录集中代表了恩施从明代以来舆地研究成果。而且令我们惊讶的是,明清恩施文人思路之广,阅读量之大——那年头,有的书籍并不好找。有时我甚至觉得,现在我们的争论,多是意气用事,并没有超过明清时代李一凤他们的水平,反而有每下愈况之感。
(三)
五峰山,西枕清江长流,东瞰柳州古城。
近年另一个争论热点是:恩施是先在柳州立城,还是在现在的恩施立城?
柳州城,位于恩施市城区东面约10公里的椅子山,它因山顶中间低平,四周较高,形如一把大圈椅而名。此山居高临下,地势险要,大有“一人把关,万夫莫开”之势。南宋开庆初年(公元年),郡守谢昌元在柳州城建立城池,设置关隘,以抵御蒙古军队的进攻。
元至元十五年(公元年)的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坚守十余年的州基山终于被元军攻破。那一夜,守城宋军刀已缺,粮已断,外无援军,后无退路,将一腔热血洒在阵前。
胜利者犁庭扫穴的暴行之后,城墙推翻了,房屋烧光了,财宝卷走了,文字记录销毁了……一段浴血奋战的历史,从此断裂,只有那光秃秃的鸡冠岩仍然倔强地在悬崖边挺立着,如同一位仍然不屈的战士期待着重新执枪上马;只有红艳艳的杜鹃仍然一年一度在岩隙间倔强地开放,似乎在为英勇的战士致以敬意。而那些可歌可泣的故事,更在老百姓心中倔强地生长,一代接一代。也正是如此,今天我们仍然能够在荒草中找到千年前的残碑断碣和即将消失的城墙,听到勇士们的传奇故事,我们能够重新审视那段历史,回想当年的金戈铁马。
柳州城令人神往,但考古专家认为,恩施城区更加古老,柳州城只是因为战事,不得已而迁建。
现在,似乎已经很难在恩施城区到宋代城址遗迹。恩施古城,主要以明代施州卫古城为基础。
明代十分重视恩施一带的战略价值,设施州卫管辖现在的恩施自治州一带。明洪武十四年,施州卫指挥使朱永拓址甃石,周长九里有余,高三丈五尺,东、北临清江,西、南环溪水的天然城堑,上设串楼、警铺、女墙,分四门四楼(城楼以城门名为名):东曰清江,南曰南阳,西曰西顺,北曰拱北。明洪武十七年八月,筑施州卫城,大规模建筑城墙和衙署。都司、左右中千户所、卫仓等,坐北朝南,沿东西街道一字排开。南门,则有施州卫儒学和文昌祠。
城东门外,建有东门渡,造清江桥。在西城墙上建野意楼,在北城墙上建太白楼,两楼相距数十步。城南药水溪建文明桥,麒麟溪建成志桥,巴公溪建济政桥,城北门外建镇武桥。
施州卫之设立,大幅度促进了恩施的经济、文化发展。施州卫世袭的军官,不仅在城中修建大型宅院,还在城外风景优美的客星山、梅溪等处,建有庄园。不少军人后代,由武入文,成为一方官绅学士。其中最显赫的是童氏家族。
童氏祖籍安徽合肥人,清嘉庆《恩施县志·人物》记载:“童昶,字明甫,本合肥人,其先人辅永乐四年调施州卫指挥,世为佥事,遂为恩施人,辅传钟,钟传璋,璋传昶……”童昶勇猛善战,在任施州卫指挥佥事时,就多次率兵,征讨土民。并在敏锐地觉察到施州卫问题所在,在齐岳山一带设梅子关、铜锣关。后因历靖州参将及淮安总镇。童昶同时博学能文,著有《施州卫志》、《大田所志》、《周正考》、《樊川集》,可惜毁于兵火,只有现在的道光《施南府志》还存他的诗歌数篇。
童氏至明末,仍然势力强盛。童天衢天姿聪颖,他写的《四癖老人传》寓意深远,文辞华美,可以说是恩施古代最好的文章之一。
清雍正十三年,施州卫一带改土归流,施州卫及下设土司全部纳入清廷版图,随之设施南府,管辖利川、恩施、建始、来凤、宣恩、咸丰六县。而清政府行事,真可谓雷厉风行,很快施南府内的土地进行了丈量,税赋得到统一,施南府及各县城池迅速建设和修缮。
清代的恩施城,经过七次大规模维修与重建。清乾隆三十六年周围丈量,计一千零三十一丈,城高高二丈四尺五寸。置四门:东门名迎恩,西门名金华,南门名朝阳,北门名拱辰。四门之上各有飞檐桅楼,楼中各有屋三楹,东门楼中建有官仓数十廒,南门楼中祀关帝。
五年前,在恩施城偶遇恩施文物局副局长刘清华先生,他热情为我当了一回免费导游,我们参观了南门外的武圣宫后,经过一条老街,到达南门。南门保持清代城墙的格局,高大的城墙拔地而起。城墙历尽沧桑,光影斑驳,令人发思古之幽情。刘清华告诉我:恩施城墙整体脉络尚存,多段保存完好,占原城墙的四分之三。东门:医院亭子,南至原棉织厂,保存较好;西门:北至西后街26号,南至学田巷13号,保存完好;南门:西至学田巷12号,东至城乡街13号,保存较好;北门:东至四维街2号,西至胜利巷14号,虽在房屋脚下,仍明显可识。
南门城墙下,古旧的房屋也保存旧貌,古风犹存。城门洞下,有烧饼铺一间。老板和很多古镇的手工业者一样,神色散淡。只是我们一摸,发现身上零钱不够时,他才抬起头来,不冷不热说声:“没有就算了。”我忍不住大笑说:“刘局长,你的面子可真大!”刘清华的面子大,那张烧饼更不小,而且味道绝美,尚未出炉,就香气四溢。咬上一口,更是酥到骨头里去了。
对我这样的吃货来说,老城的烧饼甚至比古城墙的吸引力还大。
(四)
古人修建城池,特别讲究风水。恩施城自不例外,古人总结为四句话:“五峰环其东,客星峙其西,天楼面其南,石乳拥其北。”
明清的恩施旧城,只占现在恩施西南一角。清江从东北而来,曲折绕过城北、东、东南,而药水溪从南北而来,经西门至南门与麒麟溪、巴公溪相会,然后在五峰山脚与清江相会。前不久去来凤县,在五峰山下等车,抬头看,只觉山势徒绝,危崖耸立。山脚下二水相汇,绕山而行。同行的雷翔教授告诉我,过去此地名峡口,每到涨潮时,江水澎湃,水势浩大,十分壮观。
可见,恩施旧城实际被清江和药水溪包围,形同半岛,形成“玉带缠腰”的风水格局,而峡口则是城区水口,连珠塔的修建当与风水相关。
风水之说,倒是以人为本,重在“发人”。除了官署,恩施城内文昌祠、考棚都占据好位置。而且城隍、文昌祠都经过移建,我猜测都与风水相关。而恩施城也确实是一个藏风闭气之地,历来人材辈出。
走在恩施旧城老街,稍稍打听,就可以听到饶应祺、樊增祥、尹寿衡的名字。
樊增祥,清代著名诗人,出生于恩施市六角亭西正街梓潼巷。樊氏世为武职,樊增祥的父亲樊燮,曾是湖南巡抚骆秉章麾下一名总兵。相传樊燮曾去长沙拜谒抚台大人,抚台让他参见坐在旁边的师爷左宗棠。樊总兵不知道利害,参见师爷时没有请安,并振振有词:“我乃朝廷正二品总兵,岂有向你四品幕僚请安的道理?”左宗棠盛怒,跳起来用脚踹樊总兵,还高声骂道:“王八蛋,滚出去。”不久,朝旨下,樊燮被革职回籍。
樊燮忍辱含垢带全家回到恩施,他重金聘请名师为两个儿子执教,不准两个儿子下楼,并且给儿子们穿上女人衣裤,并立下家规:“考秀才进学,脱外女服;中举人,脱内女服。”樊增祥自幼聪颖,不负其父所望,发愤苦读,一路考秀才、中举人,并于光绪三年(公元年)进士,改庶吉士。最终做江宁布政使权署两江总督。
可惜,梓潼巷樊氏旧居已经不见,飞速的城市发展,不是旧时模样。
这是八点十分的恩施,这是一个计划赶上不变化的时代。
遥忆二十四年前,我刚走出校门,呆在恩施城区等待分配。一名已经参加工作的师兄来访。他就职于五峰上的转播站,说起工作,言多牢骚。我们是学无线电的,自然知道,转播站多建于荒山野岭,在转播站上班,形同流放,而那时的五峰山确实也够偏僻。
我没有选择五峰山转播台,当然转播台更没有选择的意思,我连流放的机会都没有捞到。现在环顾五峰山,看到山上州广电局宿舍群,宛如别墅,各种羡慕嫉妒恨。事实上,五峰山已经成为一个旅游胜地,山中“农家乐”应运而生,山中餐馆林立。而外地游客的大巴车一辆接一辆,排成长蛇。
我们就餐的那家“农家乐”,造型比照传统土家吊脚楼法式,飞檐高翘。为了吸引客人,老板还在院中搭建舞台,每天定时表演文艺节目。这些节目,我们常看常新,而外地游人更觉稀奇,每个节目节目结束,掌声响成一片。
不仅五峰山变化大,恩施城区更是一天一个样,大家追求的是“黄金地段”,而不是风水格局。
坚守了数百年的老城墙,已经岌岌可危,老街和传统建筑被拆除,甚至连丹霞地貌都受到破坏,血红的山峰被一座座地铲平。老实说,我从不信奉风水之说,它如果有点作用,那就是可以适当阻止一下野蛮开发。记得四年前去重庆某县游玩,当地政府准备在一座名山修建一个现代建筑,一位朋友状如神棍,四下看了一下,阴阳怪地说:“有点破坏风水啊。”一位在旁边的官员听后大感兴趣,甚至把那们朋友尊为大师!
这是八点十分的恩施,传统与现代并行,破坏与建设同在。一些旧景点消失,同时产生一些新文化因子。
我们是一个守护者,还是只能当一个旁观者?
城下,灯火辉煌,霓虹闪烁,天上的明月也失色。这是一个美好的夜晚,想来城中的人都挤到街头,在滨江路上漫游,在大排挡上逍遥。
说起大排档,就想起多年来和恩施朋友的豪情。9年前某天凌晨一点钟,和朋友倾城在机场路酒后纵谈。后来,他写下这样的诗句:
这是一点零一分的恩施
我和地球上其他的人们一样在走来走去
这是一个没有任何表情的恩施
我努力屏住呼吸强迫自己不要太早睡去
夜渐深,我才突然发现,快零晨了。
这已经不是八点十分的恩施。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